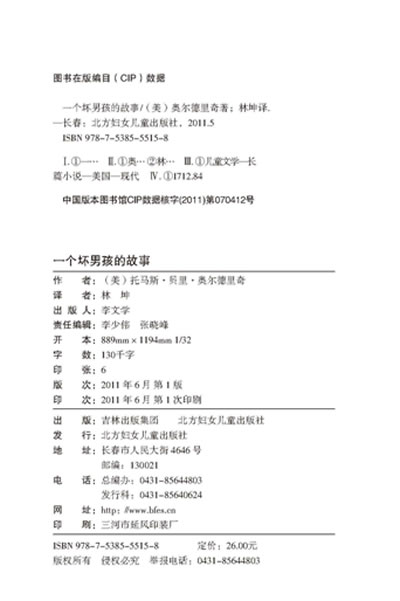一个坏男孩的故事详细介绍
-

-
品牌:其他品牌
适合年龄:3岁以上
产品规格:188页
指导价格:¥26.0
产品介绍:

编辑推荐:
美国小说之父奥尔德里奇献给儿童的励志经典 少年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中国大陆唯一版 四位美国总统盛赞:“坏男孩”教会我们坚强与勇敢
一百年总销量超过1000万 109个国家引进版权

内容简介:
《一个坏男孩的故事》用孩子的语言讲述一个“顽童”的故事,“美国小说之父”托马斯?贝里?奥尔德里奇的童年写真。淘气的小伙伴们组成了“蜈蚣帮”,并在“帮主”汤姆?贝莱的带领下,开始了他们好玩刺激的旅程:出逃、没带一分钱、火车换汽车……大人眼中的“蜈蚣帮”总是无法无天地做着恶作剧,但带给小伙伴们的却是巨大的欢乐。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快乐与体验中渐渐长大……
汤姆·贝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还是来听听主人公的原型——本书作者说的:“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孩子,新英格兰随处可见的普通孩子,跟那些故事书中一点不真实,像吸干了汁的橙子似的男孩毫无相似之处。”

作者简介:
托马斯·贝里·奥尔德里奇(1836—1907),美国著名作家,被称为“美国小说之父”。他与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是同时代人。他的《一个坏男孩的故事》曾被马克·吐温视为《汤姆·索亚历险记》的部分灵感来源。

目录:
01 先说说我自己
02 我对北方有奇特的看法
03 在“台风1号”上
04 利物茅斯
05 纳特尔府
06 光与阴影
07 难忘的夜晚
08 独立日历险记
09 加入蜈蚣帮
10 与康威决斗
11 吉卜赛女郎
12 利物茅斯的冬天
13 斯拉特山上的冰雪堡垒
14 海豚居出航
15 老友重逢
16 水手本的故事
17 我们让利物茅斯人大吃一惊
18 青蛙的相思
19 失落的我
20 我证明了自己是爷爷的孙子
21 我离开了利物茅斯
22 尾声

精彩书摘:
01 先说说我自己
这是一个坏男孩的故事。其实,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只是非常顽皮而已。我很清楚其中的情况,因为,那个男孩子其实就是我自己,更确切地说,他是过去的我。
为了不让书名误导读者,我只好赶紧在这儿向大家保证:对我这个所谓的坏孩子,并没有什么见不得的劣迹要揭露。之所以取名为“一个坏男孩的故事”,一半是因为,我要区别于那些活现在故事书中的完美无瑕的小绅士;一半是因为,我想我的确不是天使。我可以很诚恳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厚道、但容易冲动的人,我的消化能力非常好,但我不是伪君子。
我根本不想成为天使,也不想与天使为伍,对《启示录》中的宗教教条没有兴趣。《威伯德?哈金森》写得还没有《鲁滨孙?克鲁索》一半好,我只会把自己那么一点点可怜的零花钱花在胡椒、薄荷糖和威尔士糖上,而不会捐献给斐济群岛的土著。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在新英格兰随处可见的有血有肉、真实的普通男孩。我不像那些不真实的故事书上所写的,和那些像被吸干了汁的橙子似的男孩一丝相似之处都没有。好了,言归正传,开始讲故事吧。
每当有新生来学校,我总会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拦住他问:“我是汤姆?贝莱,你呢,叫什么名字?”如果他的名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就会很热情地和他握手;但是如果不喜欢,我就会扭头就走。没办法,我对名字实在很挑剔。
我觉得像希金斯、威金斯、斯普金斯之类的名字,简直就是对我耳朵的侮辱;而像蓝顿、华莱士、布莱克之类的名字,就像是获得我信任和尊重的口令。
天哪!曾经那些亲密的伙伴中,有些年龄比我大的朋友,现在已经是律师、商人、船长、军人或作家。而菲尔?亚当斯(亚当斯是特别棒的姓氏)则成了上海领事。在我的脑海里,他应该是这个样子:前额的头发剃得光光的(他的头发从来就不是很长),脑后拖着根“猪尾巴”。听说他结婚了,我希望他和他的“汪汪”小姐在一起能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跷着二郎腿,坐在挂着铃铛的蔚蓝色的塔楼上,用小小的茶杯喝着茶。
宾尼?华莱士长眠在南方的墓地里。杰克?哈里斯也去世了。在那场著名的斯莱特尔山雪战中,他指挥着我们这群年龄稍大的孩子。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我看见他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前去与被击溃的波托马可河军团会合。但这不是昨天,而是六年前的事情——在“七棵松”战斗中,勇敢的杰克?哈里斯义无反顾地冲进叛军阵中,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下。昔日的伙伴,就这样各奔东西,有的结婚有了孩子,有的却离开了人世间!我不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利物茅斯的神殿学校读书的所有男孩后来都怎样了——似乎所有熟悉的面孔都已离去!
但是用不着用力挥手召唤,我就能马上将他们从过去的岁月里唤回到眼前。我一想起他们,就很是高兴。快乐无边、魅力无限的往昔,在那美好的氛围中,就连我的死敌康威都变了模样,他亮泽的红头发上罩着梦幻的荣光。
我开始勾勒童年时代的轮廓,这是借用过去在学校里的套话。我叫汤姆?贝莱,亲爱的读者,你叫什么名字呢?无论你是威金斯还是斯普金斯,我们都会融洽相处,成为永远的、最要好的朋友。
02?我对北方有奇特的看法
我出生在利物茅斯,不过,还不等我熟悉这座漂亮的新英格兰城镇,爸爸妈妈就带我搬迁到了新奥尔良。爸爸的钱都投资在银行里了,结果却没能拿回一个子儿来。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搬家的时候,我才一岁半,够小的吧,所以至于住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都没有分别。不过,七年后,爸爸提出要送我去北方上学时,我对地方却非常挑剔起来。当时我一脚踢翻了一个黑人小男孩——碰巧他就站在我面前,使劲跺着脚,居然大声叫喊:“我绝不和那么多北方佬一起生活!”
你看,我就是那种十足的“有着南方信仰的北方人”。新英格兰在我脑海里,一点点记忆都没有,我最初的记忆都是与南方有关的——我的黑人保姆克洛伊大妈,还有那差不多没人照料的花园。我们家的房子就在这个花园当中,它是一幢白色的石头房子——它宽阔的走廊两边紧挨着街边一排排的橙树、无花果树和木兰花树。我很清楚自己出生在北方,但我却不希望别人发现这个事实。我以为如果这种“不幸”被时间和距离包裹得密不透风,也许根本不会有人记起。我从来没告诉过我的同学说我是北方佬,因为他们说起北方佬来,充满轻蔑。他们这样,让我觉得因为自己不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出生的而感到实在非常丢脸,觉得至少也应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附近地区。克洛伊大妈更是让我这种印象加深了——她说“北方绝不可能有绅士”。还有一次她真的吓坏我了,那就是她宣称:如果有哪个卑鄙白人想把她从主人身边带走,她会用葫芦敲掉他的脑袋。
这个双眼闪着光的可怜女人,她那每当说到要敲掉想象中的卑鄙白人的脑袋时的神情,竟然是我关于过去最鲜活的记忆之一。
坦白说啊,北方给我的印象,就如同现在受到那些有高素质的、与美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英国人款待时的感觉。那会儿,我还以为北方的居民分为印第安人和白人两类。印第安人偶尔也窜到纽约,在傍晚黄昏的那会儿,他们就会去把那些还在市郊逗留的女人和儿童抓来,然后剥掉他们的头皮;而白人呢,不是猎人就是学校校长。
对我来说,一年中最漫长的季节就是冬天。这会儿我喜欢那儿最流行的建筑:木头房子。在我脑海里,呈现的北方就是这样的景象。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恐慌关于我搬到北方来住了吧。也许你们会原谅我一脚踢倒了黑人小山姆,也会知道我爸爸告诉我要决定搬家时,我的反应为什么那么激烈了吧。至于说踢小山姆,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都这样,只是踢的轻重稍有不同而已。
我爸爸对我歇斯底里的反抗,尤其是满脸的惊惶感到很困惑。当小山姆从地上爬起来后,爸爸牵着我的手,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把我带进了书房。
如今,爸爸坐在竹椅上问我话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当时在他弄清楚我反对搬到北方去的原因后,他便立刻开始拆掉我脑海中的那些木头房子,试图驱散我想象中的那些东部、中部各州数不胜数的印第安部落。“汤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底是怎么被灌输到你脑子里去的?”爸爸擦着眼角处的泪花问道。
“克洛伊大妈。都是她告诉我的。”
“那你真的相信你爷爷身上裹着镶着珠子的毯子,小腿上绑着敌人的头皮吗?”
“当然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汤姆,你想气死我。”
爸爸把脸埋到了手绢里,在他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似乎心中非常痛苦。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虽然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说的话、做出的反应,会感觉那么糟糕。也许是因为我竟然认为自己的爷爷纳特尔是印第安武士,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
接下来的好几个晚上,爸爸都在给我讲述新英格兰大概的历史:它早期的斗争,它的进步,以及它现在的衰落和混乱——这些我在学校也有所了解,不过我对历史不感兴趣。
就这样,我不再反对搬到北方去,恰恰相反,我对搬到一个全新的、充满新奇的世界的旅行充满了期待,并且我激动得彻夜睡不着觉。我幻想着会有无穷无尽的乐趣和历险在等着我,尽管我还是觉得有可能会遭遇野蛮人,所以我暗自决定上船时(计划中的这次旅行是走海路),在口袋里揣把小手枪,以备在波士顿上岸时,万一碰到印第安人好派上用场。
我还是没办法改变脑海中的印第安人。不久前,彻罗基人部族才从阿肯色州被赶走,在西南部广漠的旷野中,边境殖民者主要的威胁还是红色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麻烦”一直是从佛罗里达到新奥尔良的报纸上的头条重要新闻,常常听说游人在州内被袭击、被谋杀的事件发生。如果佛罗里达常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为什么马萨诸塞州就不会有呢?
虽然离出发还有些日子,但我已经急切地想离开了。我越来越没了耐心,尤其是在我和爸爸妈妈出发前的两个星期,爸爸为我准备了一匹小野马,并已经把它运到利物茅斯。我的心因为有了小马驹(有一天夜里,我甚至梦见了小马驹,但它把我踢下了床)和爸爸许诺每两个夏天会同妈妈一起来看我,而安定了下来。小马驹的名字叫吉达娜,是西班牙语“吉卜赛人”的意思,所以我总是管它叫吉卜赛女郎。
终于,离开橙树丛中那爬满葡萄藤的大房子的时刻要到来了:我去跟小山姆道别(我相信他肯定很高兴摆脱我)。和淳朴的克洛伊大妈分别的时刻也来临了,伤心的克洛伊大妈吻了我的眼睫毛,然后用鲜艳的头巾捂住脸。为了这次分别,她特意戴上这条头巾。
我还能清楚地想起他们站在花园的大门前:克洛伊大妈脸上泪珠晶莹,山姆六颗门牙闪亮如珍珠。我对山姆很有男子气概地挥挥手,并哽咽着对克洛伊大妈说“再见”。他们和老房子渐渐远去,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03?在“台风1号”上
对这段去波士顿的海上旅途,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上船没几个小时我就病倒了。
轮船的名字叫“台风1号”,号称快速轮船,后来终于知道它只是在报纸的广告中才航行得很快。因为我爸爸拥有四分之一条船(实指拥有该船四分之一的股份),所以我们才会搭乘这艘所谓的快轮。我一直在思考,这艘船的哪四分之一是他的呢?最后我断定是这船的后甲板部分——因为我们就住在后甲板的特等客舱中,船舱顶上开着一扇圆形的天窗,舱壁上钉着两张隔板,或者说是两个座位,我们就睡在上面。
甲板上乱成一团,因为发生了许多事。船长用一只扁平的马口铁喇叭,声嘶力竭地发布着命令,却没有人听他的。船长的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像是一只挖空的南瓜,里面点着一支蜡烛。他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扯着嗓子咒骂着水手。水手们却毫不理会,只是高声喊着号子:用力划呀!举起兰姆酒啊,为西班牙美洲大陆,欢呼!
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在为“西班牙美洲大陆”欢呼,反正是在为什么事欢呼。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家伙,他们也的确很快乐。突然,我的幻想被一个像柏油一样黑糊糊的身影打断了:这个水手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五十来岁,眨巴着一双蓝眼睛,灰白的头发盘在头顶。他脱下防水雨衣,扁平的头顶一露出,让人觉得在他年轻时,有人一直坐在他头上似的。
这个男人有着古铜色的面孔,这让他显得特别精力充沛,似乎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力,使他脖子上的领巾都松开了。不过,引起我注意并让我对他有好感的是他左手臂上的一幅画:一个人头鱼身的女人。那女人一头嫩绿的头发,手里拽着把粉红梳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美的画,因此决定要认识一下这个人,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手枪去换来我手臂上也有这样一幅画。
我还站在那儿欣赏这件艺术品的时候,一艘船体上喷着几个醒目大字“AJAX”的扁平汽轮拖船,喘着气从“台风1号”旁边经过。跟我们这艘大船比起来,它那么小却又显得那么自负,简直引人发笑。同时我又想,拖船开来这里干什么呢?几分钟后,却发现我们的轮船被人用缆绳跟这小魔鬼绑在了一起。拖船喘着气,尖叫一声,轻而易举就把我们拖离了码头。我曾经见过一块奶酪被一只比它小八到十倍的蚂蚁给背着。现在看到这些,不得不让我想起那只蚂蚁来。这时我发现,“台风1号”竟被烟囱里冒着黑烟的拖船拖进了密西西比河。
船在河心打着转,我们的船好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顺流而下。但是又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轮船似乎没有动,而只是河岸、非常多的汽轮、林立的船帆器具、河岸边的一长溜的仓库,飞快地离我们远去。
站在甲板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认这可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运动。最初很长的时间里,从轮船的一侧,只能看到又低矮又潮湿的长满了矮小柏树的陆地。这些柏树上到处挂满了随风飘荡的铁兰,这样的地方最适合短吻鳄鱼和刚果毒蛇生活了。时不时还会出现一块黄色的沙洲,水面还会冒出折断的树枝,像是鲨鱼露出水面的鳍。
轮船转过一个弯道时,爸爸对我说道:“你还能看这座城市最后一眼,汤姆。”
我转过身,望着渐行渐远的城市。远处的新奥尔良已经成了暗淡模糊的影子,圣查尔斯教堂的圆顶还在阳光中闪耀着。不过,看上去还没有克洛伊大妈的顶针大。
我接下来是不是还记得点什么?我还记得灰色的天空,焦躁不安的蓝色海水。拖船早已经取掉了绳索,滑稽地尖叫着走远了,仿佛在说:“我的活已经干完了,自己照顾自己吧,老‘台风’!”
爸爸?!我们的轮船鼓起白色的船帆,像爱炫耀的火鸡似的,在海面上招摇而行,似乎为能自己照料自己而自豪不已。我一直和爸爸在轮舵舱附近站着,观察着孩子眼中最优美的一切。不过,这会儿已经起雾了,我们就下到船舱中去吃晚饭。看着新鲜的水果、牛奶和冷鸡肉片,感觉都很不错,但我却没有食欲。这时我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柏油的味道。突然,船身一斜,真的难料会不会有人把本来送向嘴里的刀叉戳到眼睛上。酒杯都放在固定在桌上的架子里,这会儿“叮叮当当”直响。悬在天花板上的四条镀金链子上的灯,剧烈地摇晃着。地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人的脚似乎踩在羽绒床上。
甲板上的旅客没有超过十二个人,连同我们在内。天黑前一个小时左右,所有的这些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船舱里,除了一个秃顶的老绅士——他是一位退休的船长。
晚饭后,爸爸和那个老绅士特鲁克船长下起了跳棋。我站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手忙脚乱地把棋子摆在棋盘上,感觉还挺有兴致的。他们下棋下到紧要关头的时候,轮船却倾斜了,棋子通通滚落下去,黑白棋子混在一块了。这时我爸爸哈哈大笑起来,特鲁克船长则气坏了,说如果这个“破鸡笼子”没有倾斜的话,他自己的棋只要再走一两步,他就赢了——他说的“破鸡笼子”就是我们乘坐的轮船。
“我……我要睡觉了。”我说道。我的手放在爸爸的膝盖上,突然有一种极其异样的感觉。
正是关键的时候,“台风1号”剧烈地摇晃起来,我一下子滚到了铺位的一侧。看到了在脚边架子上的衣服,我稍稍放心了一点——知道之前准备的手枪就在身边,顿时有了莫大的安慰,因为我断定过不了多久,海盗就会来袭击我们。这是我记得清楚的最后一件事情。后来,别人告诉我,那天半夜,我们遭遇了狂风袭击,直到进入马萨诸塞州海岸,大风一直没有停息过。
很多天,我只是感觉到剧烈地上下颠簸,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毫无知觉。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感觉。除此,我还有点模糊的印象,爸爸时常爬到上铺来,叫我“古代水手”,要我开心起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古代水手”根本就开心不起来。如果有人用喇叭对他大声喊着“一只矮矮的、形迹可疑的、桅杆歪歪斜斜的小船,正拖着我们飞快地前进”,我绝不相信古代的航海家能听进去。
有一天早晨,我们碰上了这样的事情。我在甲板上曾看见过的,装在船头的大炮“砰”的一声巨响,开火了,我以为这是在对付海盗呢。没过几秒钟,又是“砰”的一声巨响,我虚弱的手终于伸进了裤袋里。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那不过是“台风1号”在向科德海岬鸣炮致意,因为这是从南方来的轮船在接近海岸时看见的第一块陆地。
轮船不再颠簸了,我立刻就不再晕船了,完全恢复了过来。
在科德海岬,狂风连“对不起”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接下来的两天,每天在舒适宜人的天气中航行至少有七个小时,我们的领航员是这样说的。
既然“台风1号”不颠簸了,那我又可以到甲板上闲逛了。我在艏楼里找到了那个胳膊上文着绿头发女人的水手,艏楼位于船的前半部分,类似于地窖,我立刻就跟他混熟了。和我意料之中的一样,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才五分钟的工夫,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他已经环游世界两三次了,肚子里装满了说不完的故事。按照他的说法,从他出生起,几乎每年至少会碰到两次轮船失事。他曾经在德凯特① 手下干过,就是那个痛斥阿尔及利亚人,并命令他们发誓不把战俘卖去做奴隶的指挥官;他还在墨西哥战争中参加过炮轰维拉克鲁斯的战斗,并不止一次地去过亚历山大?塞尔柯克②逗留过的荒岛。航海生涯中,几乎没有他没做过的事情。
我说:“先生,我觉得你的名字不会是‘台风’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帝保佑你。我叫本杰明?沃森,来自楠塔基特岛。不过,我倒确实是个沮丧的‘台风人’。”他补充了一句,这让我对他越发敬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台风是一种蔬菜的名字,还是一种职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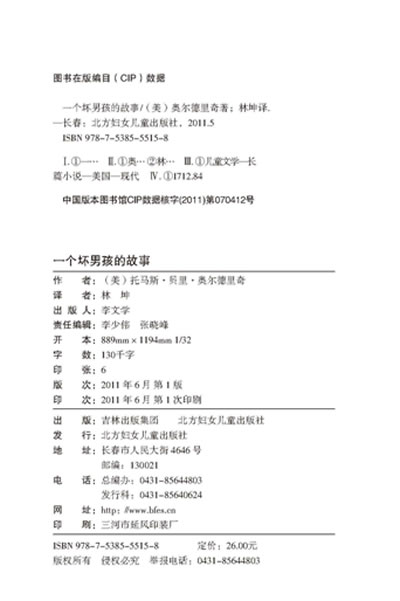
同价位日用品排行榜
孕前产品排行榜